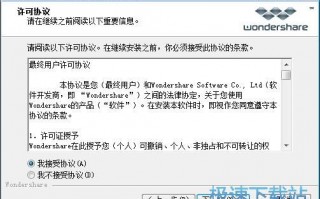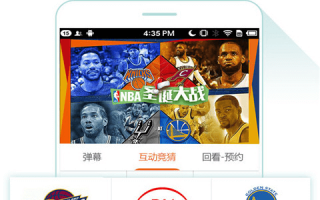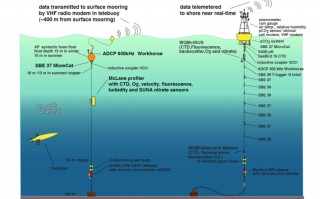他们这样回答中国古代科技“有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
■张柏春
中国古代科技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些精神都值得当代人大力弘扬。对中国科技传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外学者为此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今年是刘仙洲(1890~1975)诞辰130周年、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诞辰120周年和王振铎(1911~1992)诞辰109周年。笔者谨撰小文,纪念这三位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创建者。
刘仙洲: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机械工程教授刘仙洲参照现代机械工程学科框架,率先发现了文献和文物所反映的古代机械技术。
1935年清华大学刊印了他的拓荒之作——《中国机械工程史料》。该书分为11个部分,即普通用具、车、船、农业机械、灌溉机械、纺织机械、兵工、燃料、计时器、雕版印刷、杂项和西洋输入之机械学,勾画了古代机械史的大致范围。
1935年之后,刘仙洲一边搜集和整理史料,一边做专题研究,发表了关于原动力、传动机构、计时器、独轮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
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关于科技史研究十二年规划的座谈会,刘仙洲和袁翰青等专家在会上主张把科技史建设成一门学科。
经过二十几年的积累,刘仙洲写出一部中国古代机械史,即《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此书在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部书以机械学的学理为主线,重点阐述了中国古代在简单机械、原动力、传动机构等方面的“发明”,构建了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基本框架。
刘仙洲在“绪论”中强调:“我们应当根据现有的科学技术知识,实事求是地依据充分的证据,把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分别地整理出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早就是早,晚就是晚。”
王振铎:复原出标志性的古代发明创造
文博学家和科技史学家王振铎从20世纪30年代起,精心解读有关古机械的文献记载,并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对古机械和相关技术进行了系列的专题研究。
他先后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了几十种古代发明,其中司南、指南车、记里鼓车、鼓风器、地动仪和水运仪象台等复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也为后来学术界继续复原水运仪象台等机械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3年,王振铎复原的司南、地动仪、记里鼓车等被中国人民邮政纳入到“伟大祖国”邮票中。如今,他复原的司南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标志性图案。
王振铎的复原及相关论文是科技史专题研究的典范。他将自己撰写的“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汉代冶铁鼓风机的复原”“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和“宋代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等文章汇编为《科技考古论丛》,于1985年出版。
这些论文反映了王振铎的深厚学术功力和严谨治学方法,值得后学们学习和仿效。
李约瑟:将中国科学技术置于世界文明史中
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被誉为“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他将中国科学技术置于世界文明史中加以考察,书写“联系的历史”,包括为欧洲科学技术寻找东方来源。他与合作者从中文文献或考古资料中发现了“被中香炉”、胸带式系驾法等中国发明,在对某些发明的辨识方面,超过了其他学者。例如,他指认水运仪象台的“天衡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钟擒纵机构。
在王铃的协助下,李约瑟写出《中国科学技术史》(SCC)的机械工程分册。这部1965年出版的著作的篇幅几乎是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9倍,其中关于工匠、制造工艺及相关材料的内容是刘仙洲书中较少涉及的。李约瑟在书中引用大量的中文和西文资料,通过微观考证与宏观叙事,阐释中国机械工程的全貌。
与当时的中国学者相比,李约瑟的优势是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和对西方知识传统的了解。他偏好的叙事方式是:从欧洲技术谈起,然后转向西亚、中亚等地区,再追踪到中国,探讨知识的起源和可能的传播情况,有时采用“激发传播”等概念解释知识的互动。尤其特别的是,他以英文出版论著,起到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巨大作用。
刘仙洲、李约瑟和王振铎所做的工作具有互补性,分别解决了诸如“有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等许多学术问题。王振铎在复原古机械过程中吸收了刘仙洲的一些研究成果。李约瑟引用了刘仙洲和王振铎的论著。1956年,刘仙洲在意大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了“我国古代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一文,并与李约瑟当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学术原创往往是不完善的。例如,刘仙洲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中的个别插图标错了文献出处,王振铎复原的水运仪象台未必能完全正常运转,李约瑟有时候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不过,瑕不掩瑜,他们把握学术问题的能力和所做研究的水平不是一般学者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如何传承刘仙洲、李约瑟和王振铎等先贤的学术遗产,开创学术研究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来源: 《中国科学报》
薛凤: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就不能不提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
【近日,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薛凤女士(Dagmar Schäfer)获得2020年度德国莱布尼茨奖,该奖项为获奖者提供250万欧元研究经费,是德国最高学术荣誉。观察者网就德国汉学研究近况,以及中国科技史尤其是《天工开物》的历史地位问题等等,采访了薛凤女士(Dagmar Schäfer)。】
(采访 观察者网/ 武守哲)
观察者网: 薛凤女士您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采访您。在对明朝宋应星做个案研究的时候,认为可以通过对他的生活和著作来分析哪些“文化性”和“历史性”因素影响了科学与技术知识在中国的形成。您是否在有意解构或者重新回答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薛凤: 提及中国科技史,我试图重新寻找和发掘新的问题意识,绝非想完全解构李约瑟难题,虽然我完全赞同他的发问方式,即科学与技术思想与工艺实践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到底是怎样的。李约瑟在他那个年代名气很大,但是他受限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如同我们的眼界也同样受限于这个时代一样)和1950-198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我的研究方法旨在揭示“科学”与“技术”对宋应星那个年代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自然和文化研究中探索理性、真理和信念的方式方法。
我无意于逐一辨析某些分析方法中的各类推理假说是否出现了错误,而是尽可能地将宋应星的生活和著作的剪影放置在他原本的生活舞台上,晚明的时代关怀便是投射其上的灯光,可以让读者一同欣赏那些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关于科学技术思想的不同音调、多种多样的人物群组。我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做得很棒,保留了历朝历代的大量的文献供我们今人研究。

李约瑟(1900-1995)
观察者网: 在《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一书的前言中,您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宋应星在整个明朝中算是一个很另类的知识分子,而且在明人笔记的书面话语中匠人形象缺失的这一情况非常显著。你认为对此种历史现象的解释要避免掉入一般性叙述的谬误,可否再具体谈谈这一点?
薛凤: 我没有回避这些谬误,反而想把这个议题点出来,希望学术界更加谨慎地研究。宋应星呼吁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关注技术层面上的创新和演进,并且试图对科学技术寻找一个哲学上的宇宙论原则。宋应星对形而下的工匠技术的思考,他的思想动力并非向西方很多学人那样希望攫取财富,让自己变得富裕或者改善某一个阶层的生活,让生存环境变得更加舒适。他和他的士大夫同僚都没有把“技术革新”当做一个终极目标对待之,他所认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让他将自己的文字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关联之中,而非简单地记录工艺过程。
所以说,我们要从根本上反思“李约瑟难题”,不能把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体系和问题意识独断地嫁接到古人的思想世界,而没有考虑其历史时代背景。《天工开物》这个书名可分为“天工”和“开物”两部分,强调“人代天之功”,“天”这个概念代表了他对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总的反思,他的宇宙论哲学是以“气”论作为切入口和核心,正如他在《论气》这一章所阐释的那样,天和其他事物一样,都建立在“气”的范式上,而“气”成就了“物”和“事”。他认为同时代的士大夫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天人关系义理结构下对知识生成过程理论建构这一任务。

《天工开物》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观察者网: 在对中国科技史的叙述中,您多次提到了元朝这个朝代的特殊性,认为生活在蒙元对艺人和工匠的社会活动和实践操作的重视程度要超过以往,可不可以说,元朝被中国史学界所低估了?
薛凤: 绝对是这样的。明朝的职官制度很多都继承自元朝,蒙元时期是亚洲大陆,即西亚、中亚和东亚被打通的时代,数学和天文学在蒙元在一百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我有一本新书要出版了,在这本书中,我会专门谈到元朝的知识阶层是如何深入探讨物质生活,关注农业和手工业技术革新的。
观察者网: 当您在对比中国明朝科技发展与同时期欧洲文化的时候,提到了“跨界组合型”人物(hybrid figures)这个概念,认为这些“跨界组合型”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定位为学者,哪怕他们有匠人背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匠人的自我定位是否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负面因素?
薛凤: 士大夫阶层是中国真正的精英阶层,当然社会的其他阶层都想朝这个方向靠拢。社会地位是很重要的。自我定位不但牵连自身对本行业的认识,还有他者的反观,即别人认为你属于哪个阶层。李约瑟曾经论述过,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分化曾经对推动科学技术的改革和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每个社会等级差异的固化(比如士大夫在顶层,农民在底层)的背后还是有很多优良的混合形态。士大夫阶层排斥和鄙视技艺的实践操作,所以他们对成为某个技能行业的专家缺乏兴趣。整个社会结构对成为士大夫这一身份的过度奖励机制最终会损害其它行业的发展,有钱有闲阶层不愿意投资技能创新领域,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革新。
但我依然认为,对某个历史阶段的科学技术发展因素的探讨,都过于“事后之见”了,往往有意强化某些个体因素的短期效应,而忽视了大传统带来的缓慢的社会知识和经济形态的变革(这需要拉开很长的时间段才可能看清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代塑料材料学的发展,塑料作为一种化工材料,我们叙述其发展历程时很容易强调某种突然的天才发明和卫生学因素,并且将其和近代化学科学的发展过渡关联。但目前看来,塑料的发展史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加以研究。

宋应星
观察者网: 《天工开物》提到了很多乐理知识和乐器制造。相比其他匠人行业,中国的民族乐器的发展貌似更加合理,而且从未中断过。您认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化上,音乐在明代生活中占据相当核心的位置,这是否和古代的各种典礼和仪式紧密相关?
薛凤: 奏乐毫无疑问是在古代朝廷和民间大典中的重要的仪式性环节。而且古人认为音乐有“通天”的功能,体现的是人和宇宙的和谐感。所以当论述古代音乐的时候,我们要对知识阶层对“乐”和“天”的关系做一种形而上的和超越性的理解。
观察者网: 您在前面提到了“气”这个概念在宋应星宇宙论中的地位。现在中国学术界着重谈论“气”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中的功能,是否忽视了“气”在近代科学技术思想中的作用?“气”论如果再进一步发展,是否会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思想的萌芽?
薛凤: 宋应星尽力从物质世界的角度去论述“气”,并且他试图整合那些通过个人观察和经验无法确证的问题;他是如何在某些时候去扩展探究问题的现象学框架,调整自己的理论以保持自己的断言具有普遍性,这一点也很值得探讨。

《天工开物》中的牛拉水车
但我们必须说现代物理学和化学走的是和宋应星的理论框架相反的一条路:前者试图解释微观世界,即原子和分子的离合,后者的最终目的是解释宏观世界。或者可以这么说,现代科学必须要有“极限”、“有限”、“无限”这一系列的概念,探究是否存在不可再分的粒子,宋应星的“气”论,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葛荣晋把它归为“实学”范畴,认为这个领域确实有和近代物理学和化学相通的地方,但宋应星的“未知世界”和现代科学的“未知世界”并不是重迭的。
观察者网: 提到中国古代科技史,有一个人物是无法越过的——墨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墨子被称为中国科技史的开山鼻祖,在战国时代就在几何学、力学领域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您是如何看待墨子的思想几乎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断了这一历史现象?
薛凤: 我所在的德国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有一群学者专门研究墨子。很遗憾的是墨子的著作很多失传了,留下来的都是残篇,墨子的思想在20世纪初才被重新发掘和整理出来,这一点还有待学术界同行具体研究。

《天工开物》中的花楼图
观察者网: 当我看到本书有着海量的脚注和尾注的时候,有些震惊。您在资料汇集和文献综述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您是如何选择和权衡手上史料的呢?有没有一套独特的,坚持高学术标准的方法?
薛凤: 我所秉承的一整套高标准的学术训练来自我导师的传授,他是迪特·库恩(Dieter Kuhn)教授。2013年《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英文版正式出版,但是这个英文版其实并没有涵盖我所引用的所有中国文献,其中还包括一些德语文献,因为没有进入英语世界,所以并未给英语版的读者呈现出来。
除此之外,我还和一些中国高水平的学术界同行有着紧密的合作,比如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以及更老一辈的戴念祖、潘吉星教授等等,他们的研究和思想让我受益匪浅。
观察者网: 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相关问答
法兰西人的手.”结合古代科技史对此理解不正确的是_作业帮
[回答]法兰西人的手.”结合古代科技史对此理解不正确的是_作业帮
中国科技发展史的意义?
纵观科技发展的轨迹,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经济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的各个领域,成为生产力...